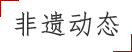
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现状
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现状
张永广 尚晓梅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湖北人民出版社)
[摘 要]在当前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青少年群体担负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路径与具体实践主要表现在:非遗进课堂、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进假期以及非遗上舞台等方面。各级部门及相关机构应加大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力度,进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青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我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致力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亟需发挥教育功能,鼓励青少年群体承担文化传承和发展重任。
一、非遗保护传承需要青少年群体的参与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的内容和形式及其有关的物品和劳动场所。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不断传承、创新和积淀的成果,蕴含着各个民族特有的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2000年4月,我国文化部正式启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估工作。经过几年努力,我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初见成效。2005年,我国政府连续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全面规划和重点部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后,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经过多年努力,现已形成由国家、省、市、县四级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
当前,我国的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时代的快速变迁,科技的迅猛发展造就了当下互联网地球村的形成,多元文化局面逐渐形成,外来文化元素加速冲击;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使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急剧改变,这使得原本植根于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因缺乏传承人而无法继续传承的境况,许多非遗项目发展受困,“危机四伏”,如不及时做好保护传承工作,很可能面临失传的危险。在当前的江南民间文化传承人群中,近90%以上的民间艺人年龄超过60岁,其中又有12位民间艺人无传承人,他们独具价值的特色技艺濒临失传。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不高,甚至有一些人的基本生活也得不到保障。现有的规章制度中缺乏对传承人生存发展权利的相关具体规定,社会公众较少关注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导致了民间技艺传承人逐渐被人们所遗忘。[1]
在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鲜有青少年身影。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为保护当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项目——越剧、沪剧等,各相关剧团拟面向全市招收几十名学员,结果无一本地年轻人报名。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是黄道婆棉纺织工艺的发源地,此工艺也因其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及形成的相关民俗,在2009 年入选上海市非遗保护项目。但时至现在,庄行镇现已无棉田,城市化进程下的农民大都搬迁到新宅,现代化的房屋结构已容不下笨重的纺织机。最重要的是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当地年轻人对这种土布纺织工艺已丧失了兴趣与热情。这项沪郊独特的民间纺织工艺后继无人,面临自然消失的命运。针对非遗保护传承中的“断代现象”,如何更广泛地吸引青少年群体积极参与其中,则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对青少年群体而言,“非遗”具有重要教育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学校课程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以帮助学生熟悉我国的传统文化,感知先贤的精神气质,进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民族精神,而且其中的各种民间艺术和传统手工艺技能也蕴含着较高的审美价值。这有助于触发学生美的意识以及提升学生对美的理解,从而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平。正因为“非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我国《非遗法》要求“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这一条款不仅第一次确立了非遗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法律地位,而且把开展非遗教育作为其法定责任义务,同时也要求教育部门及时制定相应的规定及部门规章,供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非遗教育时遵循。可见,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非遗教育已被上升为保护中华文明的国家行为,是相关机构所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随后,我国文化部、教育部和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又联合下发《关于在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的通知》。该通知得到了全国各省文化、教育部门的积极响应,各地已经初步拟定规划,着手落实该项工作。[2]正是在上述法规通知的要求下,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有了较大发展。
二、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路径与实践
(一)非遗进课堂,搭建学校传承基地
学校教育尤其是青少年阶段的校园教育,应当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主阵地。为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有效在中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普及工作,教育部和中宣部联合发起“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把每年9月设为“传承月”,通过项目推进,促使广大青少年自觉意识到中华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濒临的现状及其传承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的基础教育也在教育改革的推动下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将“弘扬民族文化,理解多元文化”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理念。这一教育理念的确立为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堂中引入非遗相关内容提供了绝好契机。[3]
非遗传承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全国各地已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在江苏省扬州市,许多非遗项目如运西中学的舞龙、汊河小学的泥塑、杨寿学校的绳艺、美琪学校的扬剧、公道小学的腰鼓、邗江实验学校的扬州民歌等,已经发展成为初具影响的精品校本课程。这些学校按照“主题学习”和“综合活动”两大领域,加强非遗项目与原有艺术课程的整合,将音乐、美术、书法等有机融合,并积极从地方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进而形成了学生喜欢、运转有效的“1+x”艺术课程体系。[4]有些学校还通过创新课程教学方式,多渠道拓展非遗教育。比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中塘学校于每周三下午开设以“非遗”为主题的拓展课,以现代化的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和创客运动作为“非遗”拓展课的有效模式。[5]
在教育领域,中央美术学院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将民间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列入大学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审美。徐州工程学院于2009年2月同徐州市文化局签订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共建协议。徐州工程学院依照共建协议,有计划地开展以区域文化为特色的“非遗课程群”建设,先后开出《徐州民间文学研究》《苏北民间舞蹈》等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共10门,初步形成了以苏北地区“非遗”为内容的特色课程群。[6]
(二)非遗进校园,丰富青少年校园文化
非遗“占领”青少年的学校时间,更积极的方式是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包括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开展校园文化节、创办各种兴趣小组等。丰富多彩的非遗保护传承活动,可以使青少年群体在寓教于乐中充分学习和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非遗”项目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中塘学校就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校园“非遗”文化艺术节。在第三届“非遗”文化艺术节上,该校还与绍兴市艺术学校合作,共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现场开展“包水饺,唱越剧,现场剪纸,现场编织,现场刺绣”等“非遗”项目展示。通过这些活动,学生的非遗技能得到提升,涌现出一批剪纸红人、竹匾巧匠、刺绣能人、陶泥高手、演唱才人、舞蹈达人。
在“非遗”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开办学生社团也是一条重要途径。“非遗”学生社团通常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教授传统手工艺技能,如剪纸协会、风筝制作协会等,这类社团一般会以专职教师、非遗传承人授课或者开展手工技能培训的方式,来激发和涵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另一类是创建譬如民族舞蹈、戏剧、音乐等艺术表演类学生社团,通过培养和扶植此类学生团体,让浓郁的艺术氛围融入校园生活。例如,为传承宁波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奉化布龙”,奉化市高级中学于2002年9月成立“奉化布龙社”、奉化高级中学舞龙队,并通过社团化管理,培训和造就一批高水准舞龙艺人,以此保护传承发展奉化布龙。[7]这支年轻的奉化布龙队之后多次走出国门,代表我国参加国际性的艺术盛会,将精彩绝伦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三)非遗进社区,丰富青少年日常生活
“非遗进社区”是指发挥其他部门积极性,开展吸引青少年参加非遗保护传承活动。近年来,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责任,各地也不断重视和推进社区周边的文化基础设施,各类各级设施先进的文化活动中心不断建成,这些地方成为青少年学生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非遗校外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课堂之外,青少年通过各类非遗活动,亲密感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和价值,改变对传统文化的漠视态度,进而增进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保护传承“非遗”责任感。
“非遗进社区”的形式主要包括:各地文化部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部署、有节奏地召集本地非遗专家、传承人结合亲身经历向青少年生动讲述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文化魅力及其现状困境,使青少年认识到非遗传承的重大意义;编辑出版图文并茂的非遗普及读物;有计划地、持续性地组织各类非遗团体展示演示活动;举办青少年非遗竞演、外出交流活动等。
上海市就成立专门机构,制定规划、拟定章程,一方面深入校园,将非遗传承保护与学科教育相结合;另一方面,走入社区和家庭,组织宣讲和活动,涵养构建青少年非遗传承梯队。经过努力,上海的青少年渐渐对非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投身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在上海,有个“上海非遗青年”小组,这个小组最初是由上海格致中学的6名学生于2016年成立,之后又利用创新思维和科技手段,在“上海非遗青年”的微信公众号上开设 “上海特色非遗信息中心”,展示推广上海各校社团的非遗传承和保护活动,成功使非遗的表现形式更加新颖时尚和具有时代气息。黑龙江的文化、教育部门则积极扶持、设立“非遗”活动基地,充分利用各级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少年宫、科学宫、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形成活动场所网络体系。[8]
(四)非遗进“假期”,丰富青少年深度体验
非遗进“假期”,就是通过在学生放假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保护传承活动,让青少年有集中的时间进行深度体验。以近年来苏州所开展的“非遗体验线”为例,苏州将每年的6月28 日定为文化遗产保护日,并开展相关活动。“非遗体验线”主要集中在苏州的县市区,包括张家港的河阳山歌、后塍黄酒酿造技艺,常熟的梅李木桶酱油酿造技艺、石梅盘香饼制作技艺,昆山的锦溪宣卷、古砖瓦制作技艺,吴江的昆曲木偶、蚕丝被制作技艺,吴中的剧装戏具和碧螺春制作技艺等。苏州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相关部门通过不同项目的展览观赏和动手体验来吸引暑期学生的深度参与。[9]广东省佛山市青少年文化宫同样在学生假期持续开展“非遗及古村落青少年文化乐游营”系列活动,将古村落游与非遗传承体验结合起来。此类活动形式生动有趣,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喜爱,改变了过去在普及传统文化时少人问津的尴尬局面。“非遗及古村落青少年文化乐游营”系列活动组织了佛山地区的青少年游览了多个特色古村落,但它并非单纯的游玩,而是与非遗传承与体验相结合,让青少年领略了茶基十番、木版年画、佛山彩灯、狮头扎作等非“非遗”项目的魅力与精彩[10]。
(五)非遗上舞台,培养青少年专业度
青少年群体在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时,更需要舞台及平台来开展效果展示,这即可以培养青少年的专业度,也会使他们获得成就感,进而更热心地从事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因此,为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青少年搭建平台,鼓励他们多上舞台展示,也是近年来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方式。以浦东新区北蔡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说书”为例,学校传承基地非常注重拓展学员的创新能力,通过组织社团,创编新剧,并积极寻找各种机会,鼓励他们走上舞台,增加锻炼机会,并且通过演出保护创新,然后慢慢地将“原汁原味”灌输给学生。“浦东说书”学校传承基地创作了适合学生的浦东说书作品作为教学内容,这些作品参加了市、区的比赛和演出,受到肯定和好评。比如,《搬新家》节目参加中国国际艺术节长三角地区故事大赛、上海市世博故事大赛,分别荣获儿童组银奖和三等奖。《中国馆》节目参加“活力北蔡”世博园区专场演出。《颂花会》节目参加浦东新区第八届学生艺术节区级艺术展演(小学组)获得一等奖,并获第二届上海市少儿曲艺大赛优胜奖和第三届浦东新区优秀童谣传征集唱活动一等奖。《合唱音画——浦东说书》节目参加浦东新区优秀童谣传唱比赛获得三等奖。[11]
三、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思考与建议
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考虑,学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希望与未来。学校教育涵盖了人的幼儿、少年、青年时期,这些时段无疑是文化学习传承的最佳时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入学校课程体系有利于学校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有利于提高传统文化素养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对国家而言,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地方而言,有利于打造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品牌,培养服务地方需求的综合素质型人才。当前的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地区某些学校的非遗教育流于空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部分学校课程中的占比较低且编排随意,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许多学校非遗课程的全部内容仅仅安排为一学期一次或两次的不定期的观摩课或表演课,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时间被极大压缩。学校教育与社区传承空间的疏离弱化了传承的实效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误区则削弱了传承主体的积极性。[12]此外,某些地区针对青少年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内容、手段和方式也过于宽泛和简单。
政府部门应重视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更少不了政府财政的扶持。对于学校非遗传承基地的建立,相关部门必须将有关法规进一步细化、落地,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学校落实的实施细则,明确把学校教育规定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重要阵地。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能否有效开展,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经费,这就需要发挥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引领和主导作用。除当地政府以政府津贴的形式给予传承人资金扶持之外,还需要建立专项财政扶持制度,给予传承学校适当的政策倾斜。
教育部门应重视完善非遗教育体系,完备非遗传承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关涉所有学校,涵盖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各级各类学校的非遗教育,包括非遗知识的介绍宣传、代表性项目展示及技艺学习、代表性项目新一代传承人的培养、非遗研究及非遗从业人员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等。非遗教育总体的开展与提高,需要跨部门(如文化、教育等)、跨机构(如学校、院团等)的合作,需要跨学科(如文化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交叉融合。[13]因此,当前亟须教育主管部门对非遗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形成共识,进而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以便于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地、推进。各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按《非遗法》的要求,制定相关规定,以指导和规范学校开展非遗教育。
具体教育机构需提高认识,重视教材编写及师资队伍建设。承担非遗保护传承具体工作的相关教育机构,理应进一步强调学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建设中应当注意尊重非遗的历史风貌,结合时代步伐和现代教育需要,适度进行创新。目前,组建专业非遗教育队伍是加强青少年非遗保护传承的关键一步。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意识,提升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感,才能真正践行非遗保护传承的使命。学校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要重视完善教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知识,要倡导教师开展关于“非遗”保护的教育工作。教师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是否丰富,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此外,学校还应注重兼职教师的聘请工作,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与学生面对面沟通,进而提高青少年对“非遗”保护传承的认知。
其他机构应加强协同合作,创新非遗保护传承活动方式。除教育机构外,各地的社区文化中心、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文化宫等机构也在青少年非遗传承工作中担负重要角色。这些机构一方面应该主动与学校对接,相互协同合作,开展内容丰富、方式灵活的非遗进校园活动,通过“第二课堂”与常规教学活动的有机结合,使非遗保护传承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进而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此类机构则需要积极占领青少年的“课余”时间,改变以往过于单一且被动接受的“公益讲座”,通过开展以“游玩和体验”为主的活动项目,调动青少年群体的积极性,让他们真实参与到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中去。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离不开青少年群体的参与。我国在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非遗保护工作原则的同时,应督促与鼓励各级部门及相关机构加大青少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力度,进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齐爱民、曾钰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校活态保护制度研究[J]. 创新, 2017(01): 99-108
[2]校外活动场所将成青少年传承“非遗”重镇[N].中国文化报,2009 -1 -11(01).
[3]张志贤. 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J].剧影月报,2008(06): 119-121.
[4]“非遗”润校园,学生亮“绝活”[N].扬州日报,2016 -9 -16(01).
[5]周苗坤.“非遗”进校 活态传承——中塘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掠影[J].少先队活动,2016(12): 43.
[6]李桂云、缪悦. 学校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02): 91-93.
[7]应伟龙.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作为[J]. 学校管理,2012(04): 21-22.
[8]校外活动场所将成青少年传承“非遗”重镇[N].中国文化报,2009 -1 -11(01).
[9]望路:“非遗体验线”可多为学生做好定制[N].苏州日报, 2016 -6 -15(06).
[10]罗晓鸣、陈启声. 传统村落游+非遗传承体验,让青少年乐享其中[N].中国文化报,2016-5 -31(02).
[11]徐东等. 浦东说书:“金北蔡”的文化新名片[N].中国文化报,2012-9-28(05).
[12]李卫英.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路径探析[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07): 44-48.
[13]李重庵. 非遗保护、文化认同与非遗教育[N]. 光明日报,2016-7-29(05).

